北京三日:见证全球最著名的三位异见人士
文/ Kashmir Hill 翻译/泡泡
这是北京一个星期四的早晨,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和世界上最具争议的技术专家Jacob Appelbaum正坐在北京东隅酒店二层的大厅里。Appelbaum喝着一杯拿铁,用叉子吃着樱桃酥。艾未未看着他。
Appelbaum是参与了维基解密,并曾参与建设匿名浏览器Tor,他带着深色的粗框眼镜,穿着印有“去你丫的国安局”(Fuck the NSA)字样的黑T恤。艾拿出了他的iPhone,放到桌下,找好角度,拍了一张T恤的照片,然后传到了Instagram上。短短几分钟之内,艾的十万粉丝里就有五百多个人点了赞。
这是三天来,艾和Appelbaum首次在纪录片摄像师罗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不在场的情况下会面。柏翠丝刚刚凭借她关于政府监视的作品《第四公民》(Citizenfour)斩获了奥斯卡,这次来到北京,是为了拍摄一部Appelbaum和艾未未一起创作艺术的短片。没有她的摄像机跟着,这俩人相处的很自然。
一时兴起,艾建议他们给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打个电话。阿桑奇最近两年一直住在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Appelbaum和阿桑奇因为工作缘故已经相识多年,于是掏出自己的 “加密手机(Cryptophone)” —— 一款安装了市面上最强劲的加密技术的定制三星手机 —— 打了电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40分,伦敦时间凌晨2点40分。阿桑奇接了电话。
“我在北京呢,和艾未未在一起。他想和你说话。”阿皮尔巴姆说。
然后他把电话递给艾。
“希望我们没打扰到你,”艾对阿桑奇说。
艾未未和阿桑奇以前从来没说过话,但是他们俩,加上Appelbaum和柏翠丝,却有很多共同点。过去十年里,他们四人披露的信息都让各国政府怒不可遏。他们曝光的政府秘密,集体地更改了上亿人的政治意识。
2008年,艾未未开始收集并公布在汶川地震中遇难的五千名儿童的名字。他们的教学楼因为是政府的豆腐渣工程而在地震中倒塌,但当时的当局拒绝承认地震遇难人数。因为他不断就政治敏感问题进行写作和艺术创作,中国当局在2009年封掉了他的新浪博客。之后不久他去了四川震区考察,却遭到警察的毒打,不得不在一个月后在慕尼黑紧急进行脑部手术。2011年,因为被控其设计公司涉嫌逃税,他被拘留近三个月,期间他被两名警卫日夜贴身监守。这一恐怖经历后来也被他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当他被释放时,当局拒绝归还他的护照,这意味着,从2011年以后他都没能再离开中国。
当艾未未被困在自己的祖国境内时,,Appelbaum,地道的加利福尼亚人,却被困在自己的祖国境外。他因为卷入透明组织维基解密而被美国的刑事大陪审团调查。他当时公开了50万份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军事机密文件,25万封国务院的外交电报,还有就是最近,据说被为朝鲜方面的黑客公布的索尼影业的邮件和文件。“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而且还在进行中。”一位司法部的发言人在邮件中说道。尽管现在对阿皮尔巴姆还没有官方的指控,但是他的律师说,如果他回到美国会“有危险”,所以从2013年起,他就一直住在柏林。
“这是不会结束的,在我看来,是永远不会结束了。”-- Jacob Appelbaum
“这种地狱般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六年了,” Appelbaum说。他在2010年首次公开和维基解密合作。“这是不会结束的,在我看来,是永远不会结束了。”
艾和阿桑奇聊了几分钟关于异见者生活的琐碎事。艾告诉阿桑奇,他希望中国可以把护照还给他,他们还比较了下各自的生活区大小。他们两个聊天的时候,Appelbaum专心地听着,脸上洋溢着愉悦的笑容。
“唯一让这一切还得以忍受的,就是我们对彼此的扶持,”他说道。
***
阿皮尔巴姆这次来北京见艾未未,是根茎网(Rhizome)的要求。根茎网是一个非盈利组织,隶属于纽约的新博物馆。过去的六年里,根茎网对七名技术专家和七名艺术家进行了配对,每对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一起创造一个艺术作品。一般来说他们要在纽约见面,不过对这两个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一个回不去,一个出不来。于是他们将地点定在了艾未未在北京艺术区宽敞的工作室里。
在艾家里,柏翠丝也加入了他们。根茎网请她来对这次会面录一部片子。柏翠丝多年来遭政府监控。2006年她发布关于占领伊拉克的电影,2012年她说自己在机场被国土安全部扣留并多次搜查,她的电子设备,采访笔记和其他资料被扣留。这些经历激发了她对监控的反对。2013年,她收到了一系列匿名来源的机密文件,这位匿名人士后来被证实是爱德华·斯诺登。她后来以斯诺登的故事制作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第四公民》,也成为了对大众监视的抗议。
因为他们的活动,艾未未,Appelbaum和柏翠丝,已成为世界上最无可非议的三个偏执狂。他们都被拘留过,艾还坐过牢。他们的生活每天都因为政府可能会报复而充满阴影。它们发出的每份公报都要被审查,每个举动都会被追踪。“当我在邮件里同时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时,就是红灯,至少你要假设这引起当局关注,”根茎网的总裁海瑟·寇可朗(Heather Corcoran)说,他也是安排这次会面的人。(寇可朗还邀请我去中国见证这次会面,并且纪实描述他们三个一起创作的作品。)
在一个专制国家,见这么一群知名的异见者,意味着要格外小心。比如买好刻录装置,免得我自己的被中国的间谍软件感染。我还在新买的个东芝上网本上用私人互联网接入安装了一个VPN,这样就可以翻墙继续刷推特(或者其他被禁的社交网络)。我还买了台MOTO-G 安卓手机,安装了TextSecure, 一款加密短信程序 (不过我后来后悔了,因为整个谷歌应用程序市场在中国都是禁用的)。最后,既然谷歌的什么服务都用不了,我就开了个雅虎邮箱。
我来中国,是想见证艾未未、Appelbaum和柏翠丝如何根据政府监控来创作艺术。我没想过他们三个之间的互相监控。几乎在他们所有的相处时间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相机。艾未未和Appelbaum还常常互相偷拍。有时候就好像艾未未的居住区变成了“真实的世界:国家公敌”版本。艾未未说他在过去的十年里拍了75万张数码照片,算是狗仔界里多产的佼佼者了。(他特别喜欢用他的iPhone 5S,还用墨玉做了一个无按钮的复制品。)
“你在脑海深处是知道你在一直被拍的。”—艾未未
艾未未在政府监控下生活的这些年,并没有让他在将相机对着别人的时候三思,事实恰恰相反。“我拍照之前不再问人家了”,艾说。“因为我们的影像在城市里一天能被记录下一百次。你在脑海深处是知道你在一直被拍的。”
***
就算艾和Appelbaum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组合在一起还是挺怪的。艾今年57岁,年龄差不多是Appelbaum的两倍,留着一撮大胡子,胡子里还是白的比黑的多。艾话不多,很沉稳,观察多于言谈。Appelbaum 32岁,精力充沛,尤其喜欢侃侃而谈那些国际阴谋的故事。艾出行的时候喜欢带着一群助手,阿在人群里会紧张。艾是个喜欢以象征主义表达艺术的艺术家,而阿是个喜欢直接行动的激进分子。
当局在艾的住处增加了监控摄像头的时候,艾把每一个都做了个红灯笼的标志。“我本想把灯笼都换成氦气球,这样的话会挡住摄像头”,Appelbaum见到艾之后不久就这么对他说。
“没必要招惹他们”,艾回答道,“灯笼就够了。”
他们两人对于个人隐私的概念也不同。艾认为他的手机被窃听,因为每次警察上门几乎都和他他收到的短信有关。不过他也相信,他大量的自我记录会保护他,因为会让警察在过多信息里疲于奔命。“我不觉得有可能避开监视”,他说。“这已经成为一场冷战了。他们下了不少功夫。我是个没有秘密的人,而他们是有秘密的。就因为他们自己有秘密,就以为每个人都和他们一样。” Appelbaum对政府从海量信息中挑选个人信息的技术很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更倾向于保护数据的隐秘。
“我不觉得有可能避开监视。这已经成为一场冷战了。”—艾未未
Appelbaum少年时期就参与了环境和动物保护积极分子的群体,后来他发现这些积极分子也能成为被监视的对象,于是开始学习隐私保护的技术。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在绿色和平组织和AV网站kink.com做IT人员,同时也开始志愿为Tor工作。2006年,他在柏林的一家黑客俱乐部——混沌电脑俱乐部遇见了朱利安·阿桑奇,到2008年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政府黑客。2013年初,他在那个匿名浏览器Tor全职做开发者和培训师的时候,他的朋友罗拉·柏翠丝收到了以“第四公民”为笔名的NSA外聘工的邮件。(柏翠丝曾拍摄过Appelbaum,之后他们就成为了朋友。)
爱德华·斯诺登泄露的那些文件让他成了全球名人。不过他们也提升了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的地位,并成为可能的调查目标。2013年6月斯诺登的故事爆出来之时,Appelbaum正在印度和欧洲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意识到他和柏翠丝和斯诺登、另外还有维基解密的联系,他知道如果他在美国的话是要被审问的。于是他决定先不回国了。虽然他还想有朝一日再回美国,不过貌似流亡的生活让他精力充沛。从那时起,他开始查阅了斯诺登的文件,并且给德国明镜周刊和其他欧洲报刊写关于他们揭露的全球间谍行动的报道。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将来源于我对政府监控的揭露”,他说。
接触本人会发现,Appelbaum比并不像想象中一个专业搞隐私的书呆子那样谨小慎微。这不像艾未未,说话的方式你就明白艾未未是知道自己是被监视的。Appelbaum不那么自我审查,并且对于新认识的人也出乎意料地很快自来熟。
“每个人都应该有隐私权,有权知道他们的邮件不会被人偷看。” – Jacob Appelbaum
“我觉得任何监视都是非法的”,他有一天和我这么说。“每个人都应该有隐私权,应该知道他们的邮件不会被人偷看,哪怕他们是佛格森的警察那样的坏人。”
尽管Appelbaum笃信个人的隐私权利,但他认为有权有势的大机构却不持有同样的权利。他说,维基解密发布索尼影像的员工邮件时,是完全合情理的。“那帮种族歧视的混蛋?”他说,指的是索尼老总艾米帕斯卡和导演斯科特·鲁丁的邮件。邮件里他们嘲讽奥巴马倾向捧黑人演员的事。“他们太无知了。”
“对中国的认识和实际不符”,他说。“中国看起来并不像是个那种压迫的监控国家,它被西方妖魔化了。”
Appelbaum意识到他刚刚称赞了一个威权政体,于是补充了一句告诫。
“好吧,他们(中国)确实有摘取人器官的“死亡货车””,他说,“但是他们并没有过分地限制。”
根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貌似器官摘取今年也被叫停了。
***
我在北京访问三天,天上飘着杨絮跟下雪一样。它们落在我的外衣上,头发上,我张嘴的时候还会飞到我嘴里。艾的助手和我说,这是中央规划,在市内种植杨树,可以让城市迅速绿化起来。尽管他们并没意识到可能以后每年春天都会有那么一周满天飘絮的时候。这是一个错误决定,不过现在制度化的这么严重,只有外国人才会抱怨这个。
艾并没有被中国政府对异见者的镇压恐吓到,但是他确实比以前谨慎多了。他6岁的儿子艾老去年和妈妈一起搬去了柏林,因为他们不希望他生活在一个压制性的政权里。艾未未以前每天都和儿子去公园散步,现在却只能每天两次视频聊天。
我在他一次视频之后看到艾未未,他明显很难过,眉眼低垂,指头摸着额头。他跟我说他想拿回护照,这样就可以出行了,尽管这意味着避免会激怒政府的行为。“他们非法拿走了我的护照,跟我保证过很多次会还给我”,他说。
谷歌和推特等公司曾经在政府要求下提交了Appelbaum的个人资料,艾未未觉得他的网络生活也是暴露在政府的显微镜下的。自从政府2009年下令关闭他的博客,他现在主要的社交媒体就是Instagram和推特了。尽管他最近仅仅只是转发别人而已。他说他不再发推特了,转而进行长文写作,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同时,他的律师浦志强,一位代理了多个异见者的人权律师,因为发微博“寻衅滋事”而被捕。现在浦志强已经坐牢一年了。
这三个人里,柏翠丝需要担心的事最少。自从《第四公民》受到广泛好评,她的名气成为了一个挡箭牌。她搬回纽约,准备在惠特尼博物馆的个展。虽然她每次过境之前都会再三确认电子信息都被加密,她现在还没有在海关出过状况。斯诺登时期的疯狂,现在也似乎回归正常态了。
“我刚开始收到斯诺登的邮件的时候,焦虑的都耳鸣了”,她告诉我,“有时候耳朵里的嗡嗡声太响我,我都没法思考。不过现在自从影片出来了以后,我的耳鸣就好了。是我的身体跟我说‘好了现在没事了’。”
这三个人虽然都在被监视,但是他们的对策却各有不同。艾的对策主要是自我审查。“你不会把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诉外界”,他说,“因为[说太多]会让你的情况更糟。”柏翠丝,记者界的翘楚,用她的拍摄技能去展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隐私是不存在的。“我没像未未那样受这么重的创伤”,她说,“尽管我觉得我已经内化了‘监控正在进行’这个事实,像福柯说的那样。” Appelbaum,这个用代表“无政府主义”的圆圈A给自己签名的人,选择走地下道路 —— 在揭露政府侵犯隐私的时候,使用密码技术,保证交流的安全。
“我已经内化了‘监控正在进行’这个事实。”— 罗拉·柏翠丝
“我的目标是,二十年以后 ,再没有美国人能说他们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说。
***
艾未未是在美国很有名的艺术家 ——他在恶魔岛的展览门票提前几个月就售空了。他还凭借《永不认错》和《假案真办》纪录片两次获奖。但是在中国,他倒没什么名气。在北京的街头看到他,也没人会盯着看或者低声讨论。只有回到酒店,国际游客们才举着手机排队想见他。
周一早饭之后,三个人一起去了附近的公园。路上他们进了一家音像店,想买《第四公民》。结果店里只有一张盗版的。封面上写着影星奎因·莱提法和科蒙。艾问音像店员工这个电影怎么样。
“还行”,员工用普通话回答道,并不知道电影的导演正在看着他。
柏翠丝和Appelbaum早就认识 ——他们在柏林就是邻居和合作者 —— 但是艾和Appelbaum并不熟,只是见面前互相谷歌了下(或者‘必应’了下,鉴于艾用不了谷歌)对方的信息而已。艾在Appelbaum到来之前才看了《第四公民》,在里面看到了他的出镜。尽管他们这次面临着工作任务 ——48小时之内创作一个有意义的艺术作品 —— 他们三个倒是成了朋友。
他们的会面中也有因文化差异带来的紧张瞬间。有一次Appelbaum让艾未未在公园里摆个姿势照相。“我要把夹克脱掉吗?”艾未未问到。“全脱了吧”,Appelbaum说。结果艾未未把衬衫也脱掉了。Appelbaum也照做了。俩人都光着膀子站在树丛里,谁也不知道这是到底在干什么。“你把衬衫脱了干嘛?”拍完照片之后,艾未未问Appelbaum。
作为异见人士面对的危险有时会在谈话中显现出来。午饭吃完了鸡爪子、烤鸭、臭豆腐和拔丝苹果,Appelbaum问艾未未愿不愿意和他一起为希拉里克林顿做一个竞选视频。
“你们要投给希拉里吗?”柏翠丝问到。
“她会把维基解密的每一个成员都赶尽杀绝的,我最后会被无人机打死。” Appelbaum说,“不过她社会事件处理得很好。我所有的那些想打胎的女性朋友的都能如愿以偿。”
听说做竞选视频,艾未未摇了摇头。“他们都一个德行”,艾如此评价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好处是这样会比较稳定。不过他们都一个德行。”
***
周二早上,这一伙人来到艾未未的工作室。他们穿过一扇亮绿色的门,进入到一片种满草和竹子的庭院,四面是爬满常青藤的灰墙。有几只猫悠哉地散步。这本该是片宁静的景象,要不是院子那边挂着一个巨大的霓虹灯的话。霓虹灯是四个字母拼起来的:F-U-C-K(发课)。庭院的另一边,有十五个白色细条纹的富士康制服挂在一条铁丝上,僵硬地随风飘荡。(富士康是中国最有名的电子设备加工厂。)
“做iPhone的人不应该穿这么可怕的东西,”艾如此评价富士康的制服。
富士康之作是要运往瑞典的。艾的团队在工作室里面做好艺术品,然后他的员工过去安装。“我无处不在,却也无处可寻”,艾说道。“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妙处。”
“我无处不在,却也无处可寻。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妙处。” —— 艾未未
工作室后面的一个白色的大房间里是尚未完工的作品。有一张放大的自拍,是艾未未在酒店电梯里和一个警察一起。这个警察刚刚袭击过他,并且造成他的脑部损伤而不得不进行紧急手术。艾未未指着一组画着用竹子做的动物骨架的彩色纤维画,说道,“我就像是这竹子一样,被无形的力量扭成各种形状。”
终于,该聊聊正事了。艾未未和阿皮尔巴姆要联手为根茎网的纽约展览做一个艺术作品,柏翠丝要把创作过程拍摄下来。
这一周很漫长,所有这些骚乱让艾未未和阿皮尔巴姆又累又紧张。不过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他们收集了材料,搞了一个六人的流水装配线,开始制作。柏翠丝端着摄像机在后面。
我不能详细的告诉你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作为观摩他们的艺术创作过程的条件,根茎网不允许我在五月二日的“七对七”会议上和其他队伍一起展出之前吐露作品内容。这个条件很让人无奈,但也是必需的。不过我要说,他们的作品结合了Appelbaum强烈的散播信息的渴望,和艾未未想要隐藏信息的渴望,有着以小见大的意义。
(编者注:艾未未和Appelbaum的作品是八只装满斯诺登暴露文件以及一张SD卡的玩具熊猫)
他们做完项目,走出工作室的时候,Appelbaum感谢了艾未未与他共度的时光,并给了他学习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帮助来翻墙,找我。”他对艾未未的员工说。“我为Tor工作。”
他们离开时,柏翠丝拥抱了艾未未。她搭着他的肩膀走到院门口。“我希望很快会见到你”,他说。“在世界其他地方,柏林,或者纽约,或者慕尼黑。”
艾未未回答说:“我觉得这不会在近期内发生。”
***
Appelbaum和艾未未结束了和阿桑奇的谈话后,我和Appelbaum打车去了机场。他和柏翠丝要去香港参加《第四公民》的首映式,Appelbaum力劝我同去。不过我已经受够了异见者的生活模式 ——那种被当作潜在监视对象的感觉,怀疑谁跟踪了我们,或者假设某人跟踪我们。
我十一点抵达机场,国际航班中午起飞。当我迅速穿过机场的时候,我对于那些需要进行的安检措施比以前更小心,也更紧张。中国海关会不会知道我过去三天都在和中国最著名的异见者,还有斯诺登的密友一起度过?他们会不会拘留我呢?会不会抢走我的笔记?还是更糟?
过关的时候,我慢慢走过体温监测系统,一个测我有没有发烧迹象的设备。我进入中国的时候有中国海关给我拍了照片,现在在我出去的路上,站在海关的相机前又给我拍了一张。我不禁感到恐慌。如果北京机场也用人脸识别技术,这些相机肯定也会检测出我的焦虑。
作为一个报道隐私的记者,我还是挺疑心的。我电脑的前置摄像头被我贴了东西挡住了;我有个PGP密钥与人进行加密的邮件交流;我要是用公共Wi-Fi上网,也会用VPN。
但是我并不完美。很多时候我也愿意牺牲隐私来换取更多便利,而留下可循的数据痕迹:我会用Facebook;我有西夫韦的优惠卡;我的伴侣也知道我的手机解锁密码。
我在北京机场托运行李时,我对于这种隐私的缺口反而感到诡异的冷静。因为像Appelbaum和艾未未那样的生活——时刻处于疑心之中——是无法长期维持的。那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监狱,一个被当局控制着的圆形监狱,甚至在当局都没有在看你的时候。
艾未未、Appelbaum、柏翠丝还有阿桑奇都找到了他们觉得舒适的隐私水平。但是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完全的隐私就代表着孤身一人。而且就算这样,也不会完全阻止监控。我们的信息太多,自己已经无法控制。在这个世界舒适的生活,就要找到一个对你适用的隐私平衡点,也要知道你公开的信息可能会被用来对付你——但希望这一切永不发生。
在机场,我安然无恙地过了安检。金属探测器的警报确实叫了,不过那也是因为胸罩的钢丝圈而已,所以他们立刻就放行了。之后我不禁开始奔跑起来——不是因为担心有人在后面追我,而是因为我马上就要误机了。我准备好回家了,能够回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欣慰。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Fusion,中文由泡泡翻译,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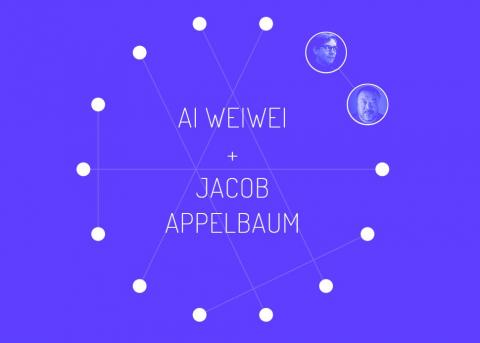








评论
StevElug (未验证)
星期二, 06/04/2019 - 09:02
永久连接
Forum Achat Cialis Stevprople
Canadian Pharmacy Brought By Echeck Kamagra Prix Moyen <a href=http://elc4sa.com>online pharmacy</a> Viagra Hard Tumblr
冒个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