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为什么经历文革十年的那代人至今“执迷不悟”?
(泡泡特约)网上经常会流传出一些关于当下中国中老年群体怪异文化现象的视频,它们所透露的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中部分人士对灾难十年的迷恋。观察者对此感觉诧异,众所周知,文革运动令所有人都成为了受害者,施虐和受虐角色在同一个人身上的轮换是其最典型的特征之一,然而很多文革幸存者显然至今都没能摆脱受创惯性,大跳忠字舞、延续旧有的权威崇拜,这些仿佛与世隔绝的现象在信息高度流动的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合逻辑。
多年来人们给出了不少解释,从洗脑的威力到人格问题,从“坏人变老了”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一个明显的主要原因一直被忽视 —— 经历者在文革结束后无一接受过专业的心理康复辅导,并继续沉浸在党文化一家独大的社会环境中。在他们潜意识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革并未结束,而高调崇毛等一系列行为则是受创者对“心理情境”之延续的一种表现。
人类对暴行的一般反应是将其排除在意识之外的,这是一种应激反应,会让深陷其中的人获得一些心理安慰,也是某些违常经历恐怖到让人难以清晰地表达出来。痛苦被偷换了,被大脑的逃避性制造出来的幸福感所遮蔽,不少人至今都在怀念毛时代,他们有可能是真的在怀念。
这是所有创伤经历者的共性。无论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个人和社群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受虐妇女和政治犯之间,独裁政府建立的大型集中营和家庭暴力建立的隐蔽的小型集中营之间,在此都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

协助的难度和基本思路
暴行拒绝被掩藏湮没。否认暴行存在的欲望虽然强烈,但自身认为否认于事无补的心态同样强烈。想要重建社会秩序,让受害者得到应得的抚慰,首要任务就是要揭露暴行,揭露真相。
受害人最具标志性的矛盾心理就是:既希望抹去受害记忆“翻过这一页重新生活”,同时又很希望将其公布于世,这是心理创伤协助中面对的主要冲突。幸存者通常会高度情绪化、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诉说惨痛遭遇,而正是这种方式损伤了他们的可信度,他们自己也被迫进入了究竟是不是要说出来的两难困境。
文革运动中这种状况尤其突出,由于很难找到从始至终绝对正义的人,如同很难找到纯粹的受害者,大多数人都扮演着多重角色,人类具有不擅长正视自己的通病,于是经历者所描述的记忆、甚至忏悔的片段,都很容易脱离事实,这便愈发加重了康复的难度。
只有彻底认清真相,幸存者才有可能迈向康复之路。可惜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保持缄默的心态赢了,创伤经历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精神状态的方式行诸于外。
那些经历过迫害而被周边人认为“变了”的人们,其心灵受创程度已足够深刻,受创者会交替出现麻木无感和创伤事件重现两种不同的症状,这种对立冲突点引起时有时无的、复杂的意识形态改变,就是精神病学家称之为“解离 dissociation”的症状。
甚至目击者也和受害者一样,受到由创伤引发的对立冲突的折磨。目击者很难保持头脑清晰并冷静以对,很难对即时事件以整体性的观照,很难记住所有细节,也难以将细节串联起来,更难的是要找到适当的并有说服力的言辞将事件真相传达给他人。因此,这些目睹暴行的人也要承受被质疑的风险。当有人公开说出暴行见闻时,他也可能要承受类似受害者所蒙受的污名。
对残酷暴行的认知会周期性地成为公共议题,但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否认、压抑和解离反应并不会只发生在个人身上,也会发生在整个社会的层次上。
临床医生都知道,当被压抑的想法、感觉和记忆浮上意识层面时,通常会是一个洞察心理创伤的良机,这样的时机会发生在整体社会的历史里,也会发生在个人生活中。
长期生活在恐怖情境中的人,其所蒙受的心理创伤是可预期的。创伤造成的异常范围有一个光谱,从单一巨变事件的影响,到长期不断受虐的复杂影响。既有的精神疾病诊断观念通常难以识别受创对个体的冲击。由于创伤性症候群有很多相同的基本特征,因此复原过程也存在大致相同的途径——主要阶段为:建立安全感、还原创伤事件真相、修复幸存者与其社群之间的关联性。
“战争和受害者都是社会急于忘却的,任何痛苦和不快都会被覆上遗忘的纱幕。我们能看到两边的正面冲突:一边是受害者,他们可能想忘掉,却忘不了;另一边是那些极力想要遗忘也成功办到了的第三者……其实对两边而言都是非常痛苦的,而弱势一方,在这场无声且不平等的对话中,永远是输家”。—— 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创伤问题研究专家 Leo Eitinger
为什么中国社会的 PTSD 问题难以解决
前段时间,一则旧消息被中文网络翻了出来,并当作笑话在传播:《柳叶刀》月刊通过中国4省超过6万人的调查数据得出中国17%的人存在精神障碍,并推算中国存在1.73亿精神疾病患者(见下图)。其实17%的比例并不奇怪,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精神疾病当属 ptsd,文革、八九屠城、维稳时代长期的政治骚扰和政治迫害、父权主义家暴、性侵、家长制的童年压迫、参加过各种战争的退伍兵…… 这还没算上各种大型的致命的自然灾害,如汶川、唐山。不过调侃17%的段子中,说者很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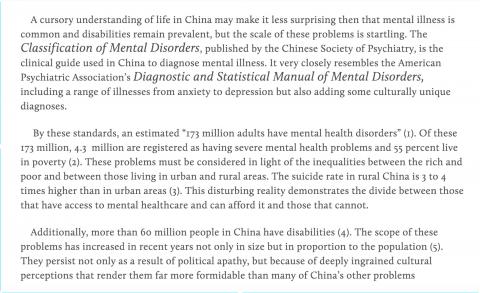
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没这个概念,甚或并不认为幸存者的表现属于精神疾病。为什么会这样?先讲两个故事。
法国神经病学家 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是歇斯底里症研究的开创者,他曾经工作在法国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一间古老的医院,这里一直是社会底层无产阶级的收容所,接纳的都是乞丐、妓女、贫困潦倒的精神病患。很多才华横溢野心勃勃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科医生都是沙可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几位就是:皮埃尔让内、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
在那个年代,没人相信歇斯底里症,就像如今的人们嘲笑文革经历者、遭受监禁和酷刑出狱后精神错乱的政治迫害幸存者,那个年代的人们对歇斯底里症患者有着同样的态度。也因此,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项研究事业来做。弗洛伊德曾因此盛赞沙可的工作,称他重建了这个议题的尊严。正是沙可的工作让很多人改变了对歇斯底里症的嘲弄态度。
沙可是幸运的,因为他恰逢一个得意的社会背景。
19世纪的法国最主要的政治冲突就是拥护既有的宗教结合君主专政的人,与拥护政教分离、主张建立共和体制政府的人之间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冲突造成了七次政府垮台。随着1870年第三共和的建立,崭新但脆弱的民主政体的创始者发动了一场富有攻击性的运动,以巩固自身权力基础,并打击和削弱他们的对手——天主教会。
这个时期的共和政府领导人都是些白手起家的男人,属于新兴中产阶级,他们视自己为捍卫启蒙运动传统的代表,他们的对手是贵族政治和神权政治。主要政治斗争是争夺教育的主导权,意识形态的斗争则是男人的忠诚和对女人的所有权。而沙可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商人,他自己则是这个新兴中产阶级精英中的精英,他家的客厅就是第三共和政府一些达官显贵的聚会场所。
沙可和官场上的同僚都极力宣扬去宗教化的科学观念,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正是用来证明去宗教化观念体系比宗教体系正确有用的。因此,19世纪末法国社会有了这个庞大且具有政治性的理由,才激起了对歇斯底里症的热切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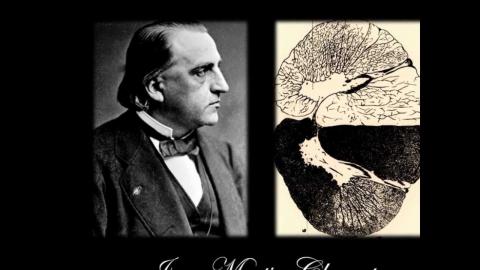
然而,时间进入20世纪后,这种政治推动力渐渐消散了,不再有任何充分理由让男性科学家继续维持研究的初衷。沙可从歇斯底里症的世界中撤退出来,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合作者 约瑟夫布洛伊尔也从对女性的情感依附研究中退出了。
随后,弗洛伊德也从心理创伤的研究中退出了。由此成为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他的改变论调被对手攻击为个人怯懦的表现。其实不无道理,怯懦是有时代背景的,在当时,任何知识的跃进都会被视为孤独的普罗米修斯般的叛逆行为,不论他的论点多么的强有力、观察多么的有效,在一个缺乏对研究课题支持的社会氛围中,他的个人努力一文不值。
唯一有可能对此予以支持的就是当时正在萌芽状态的女性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恰恰严重威胁到弗洛伊德所珍视的父权价值观。让弗洛伊德的政治信仰和女权主义运动同流,是绝无可能的,他选择了心理创伤研究与女性划清界线。
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就是学术进入PTSD研究的门槛。然而在当年就这样被荒废了。在美国,退伍军人中高达1/3的士兵患有不同程度的PTSD,社会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有8.9人,而退伍军人则达到每10万人中至少18.7人,是普通平民的两倍多。为治疗PTSD政府花费了大笔金钱,然而依旧有大半患者没能接受正规协助。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也非常晚,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军方和社会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这些PTSD患者属于诈病—— 是个人懦弱和对敌人的胆怯的表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治疗策略依旧是,追求最快速的将军人重新送回战斗岗位。只因那个时候,整个社会被以战胜为荣的爱国主义情感驱动着,没人在乎“逃兵式的”的心理疾患。
直到越战之后,对战争引起的长期心理影响才有了系统且大规模的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研究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军方或医学界,而是一群心怀不满的退伍军人有组织的努力。
这个组织名叫“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这些反战的退伍军人组成了所谓的“交谈团体”,在与战友的私密聚会中重述和再现创伤过程。他们不愿向政府机构寻求救援,他们要待在自己的地盘、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听任摆布的病患。

“交谈团体”有双重目的:1、给予受到心理创伤的退伍军人以精神上的抚慰;2、唤起社会对战争效应的关注。正是他们的证词,激发了社会对战争带来的长期心理创伤的注意,这是个非常出色的社会运动。
反战运动的道德正当性和全国笼罩在不名誉的战败气氛中,使得社会承认战争造成长期心理创伤后遗症这一突破变得可能。1980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心理创伤独特症候群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诊断项目。
我想说的是,要让创伤的事实达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意愿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和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对社会大众而言,这种社会背景要靠争取弱势群体发言权的政治运动来创造。
因此,对心理创伤的系统研究也需要倚靠社会运动的支持,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可能进行公开讨论其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这是个双向作用力,研究反过来也会促进社会对“送年轻人上战场”的质疑、认清女性和儿童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通过理解政治犯的精神疾患来认清独裁政府的政治迫害所造成的灾难,从而联合起来对抗社会上的否认和当权者的噤声要求。
如果没有要求人权的强大社会运动,没有积极的挺身而出做见证的行动,这类研究将无可避免的被压制和遗忘所取代。PTSD患者最典型的压抑、解离和否认的现象不止存在于社会意识中,也存在于个人意识里。
在中国,如果没有抵制暴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就不会有对遭受政治骚扰和迫害的PTSD患者的有效协助,如果没有对文革运动的深刻反省,文革经历者就很难接受到合理的协助,如果没有冲击父权制家长制传统的社会运动,对家暴和童年迫害受创者的抚慰不过是隔靴搔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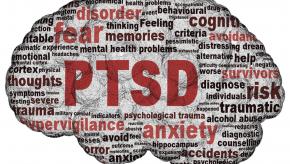







评论
Jeaacalay (未验证)
星期一, 04/22/2019 - 09:59
永久连接
Does Keflex Help Bronchitis JeaPriods
Cephalexin Altace Zyprexa Postitive Direct Coombs <a href=http://lapizmoon.com>cialis 5 mg</a> Effects Expired Amoxicillin
StevElug (未验证)
星期六, 06/01/2019 - 04:20
永久连接
Kamagra Is It Legal In Uk Stevprople
Que Es Viagra Soft <a href=http://banzell.net>viagra online prescription</a> Cytotec Prix Tunisie
Kelpaycle (未验证)
星期六, 06/01/2019 - 18:58
永久连接
Cephalexin Without A Prescription Kelpaycle
Viagra Rezeptfrei Versandapotheken Purchasing Amoxicilina With Next Day Delivery Cialis Generico En Andorra <a href=http://mpphr.com>achats priligy pas cher</a> Promethazine In Canada Amoxicillin Dosage In Chicken Feed Propecia Does It Work Hair Growth
Ellincuse (未验证)
星期三, 06/05/2019 - 11:33
永久连接
To Purchase Cialis In Australia Ellnoug
Kwikmed Coupon Code Costo Viagra Cefa Tabs Without Prescription <a href=http://cialtadalaff.com>cialis 20mg for sale</a> Cialis 5 Mg Prescrizione Medica Over The Counter Metrogel Acheter Cialis Bon Marche
冒个泡吧!